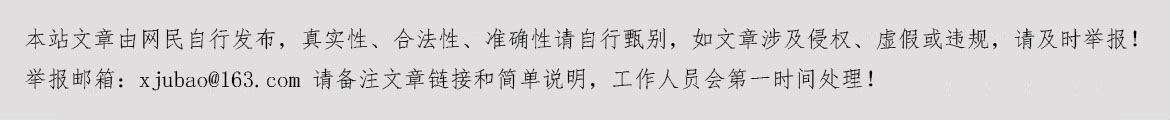授权转载自:INSIGHT视界
微信号:weinsight
原作者:李微明
无论对于高考生还是留学生,退转学生都是小众群体。
他们通过高考考入国内大学,在就读后选择退学或转学出国。
谈论起出国目的,被采访的学生认为教育无法评判高低好坏,对转学的选择充满个性化,是从个人出发的考量。
“就像谈一场恋爱,”于2010年退学留美的秋林笑道,“你很好,我也很好,只是我们不合适。”
再次听闻秋林的消息时,我刚办理完退学手续,正在回家的路上。
身旁的车座满满当当堆着从宿舍搬离的物品,我和爸妈说说笑笑,气氛轻松。
“当初秋林考上这个学校我们还觉得挺好,没想到你要退学。”父亲从后视镜中看了我一眼,说道——秋林跟我住在一个家属院,大我八岁。
“她在这个学校毕业了?”我很诧异,秋林在北京重点高中名列前茅,稳上清北的威名我有所耳闻。
“没有,她也退学了,去了美国。”母亲回答道。
2010年,秋林高考发挥失常,以两分之差落榜清华。她拒绝了专业调剂,以远超第二名的文理科最高分被另一所院校录取。在父母的劝说下,她开学后入读了一周,之后就不再去上课了,转而申请出国。
“感觉课程设置还有师资跟高中都有差距,你理解吧。”在阔别多年的通话中,她对我说。
同秋林一样,我初高中六年都在海淀区重点中学,无论正课、选修课还是学术讲座都有很好的体验,学校与大学难度的课程连接紧密,年轻老师名校博士学历居多。校外的朋友评价道:“那就是一所顶尖大学。”我当时觉得是个玩笑,现在却略有认同。
优质高中提供的资源和交际平台助力了个人发展,却也使在我面临高考失利时产生更强烈的落差感。
大学开学当天,我在最后一刻报了到,父母叮嘱我多融入学校,我答应了。
傍晚我在教学楼里熟悉环境,发现校区没有图书馆,只划出几间教室和一段走廊摆放桌椅,“这样也不错,”我安慰自己,“挺亮堂的。”
第一周的课对我来讲同样难熬,几乎每位老师在点我回答问题后都会问上一句,“你哪个高中的?”,之后又会追问一句,“你怎么到这儿来了?”。
“高考发挥得不太好。”我只能尴尬地笑笑。
我没在大学遇到高中校友,这根刺钉在心里,每一次老师的询问,教室四起的哗然和异样的目光都会使它扎得更深些。
随着与高中同学断联,我变得沉默和焦虑,却没有试图挽回——交往朋友需要共同话题,学校差距大,资源差距也大,逐渐就没什么可聊的了,这都是正常的。
第一学期结束,班会上辅导员叫我站起来,说我是专业最高分,我感到了恐慌。我失去了前方的榜样,对我而言这个处境十分危险。我害怕有一天自己沉迷于虚构的优秀,彻底迷失自我定位和上进心。
抱着这样的想法,我觉得自己需要去寻找新的、更合适的平台。
认识陈最是在英国大学的新生讲座上,身边来自荷兰和意大利的同学热情喊话,说还有一位人文艺术学院的中国人。
经过周围同学层层引见,我向左转头,看见了坐在后排的陈最。她化着精致的妆,神情冷漠。我尴尬地隔空伸手虚握了握,她直视我,微点了点头。
我们并肩坐在了第一排,互相没有说话。身后有同学小声笑闹,陈最打开褐色的线装笔记本,我侧头看着她用细管黑色记号笔列好标题,画好括弧线,规整地用打印体写下英文,忍不住问她:“你参加过高考吧。”
2017年,陈最考入985大学的文科通修班。学校设定第三年再分出具体专业方向。经过一年体验,陈最觉得自己不适合通修培养。
“之前觉得通修是很不错的搭配,结果入学后同时学中文、哲学、艺术三个大类,感觉分身乏术。我的兴趣被分散了,就对什么都没兴趣了。”她说。
学习热情的消退敲响警钟,陈最觉得不能再等下去了。“我适合更专业、更紧密的本科培养计划。”陈最说,“英国高校的课程设置学术性更强,安排更紧张,适合我百分百投入专业学习。”
大二上学期,陈最办理退学,准备申英。
我问陈最,“你什么时候确定学艺术史?”
“初中”,她答道。
陈最从小学习素描和水彩。十四岁那年,她飞去纽约,前往大都会艺术博物馆。展馆内一幅17世纪的荷兰风俗画成为陈最的艺术启蒙,“维米尔的《持水壶的女人》,我看到这幅画的第一眼就被震撼了,它完全颠覆了我学习绘画的方法。”陈最在手机上翻到当时的照片,展示给我看,“它对我是全然陌生的,但很微妙,我感到被连结了。”
在充满力量的时刻,解谜画作的愿望倾倒向陈最。她决心研习艺术史,这是她探索、体悟艺术的媒介。
如同陈最热爱艺术史,我爱文学。
上小学时,我用右手写数学作业,左手悄悄翻《穆斯林的葬礼》。十三岁时,我写信给十年后的自己:“你好,你过得好吗?考上梦想中的中文系了吗?”高中毕业后,我报了中文专业,以为自己终于解放了,可以每分每秒投入文学,再也不用为其他不感兴趣的科目分心劳神。
现实并不如人所愿,大一通识课多,学校一周只安排一节专业课,并规定文科生只能选理科通识。拿着大学课表,文、理、英语、体育、计算机揉在一起,我看不出自己的专业。我渴望专注于专业学习,而不是在修习文学时花更大量的时间去背化学方程、练习计算机基础代码和足球射门。
家里明确表示不支持本科留学,我没再跟父母商量,自己边查词边逛遍了英美多所高校的官网。经过对比课程设置和培养方案,我觉得英国高校围绕主专业设置的课程方案更符合自身期望。
大一结束后,我用一天时间办理了退学,在假期中读着英国大学发来的书单,同时准备出国手续。
得知我在撰稿,高中同学章闰水向我介绍了余觅,他们是微信转美群的群友。
作为我的第一个采访对象,余觅直接粉碎了我对退转学学生的片面印象——退转学的原因不仅是月亮,也可能是六便士,或是在月辉映照下的六便士。
对比我和陈最,余觅无法完全将追寻梦想作为留学目的。
她生长在山东沂水县,家中以父亲跨县做小生意为生,面对留美高昂的费用,家庭经济压力很大。余觅认为自己没有太大志向和情怀,在她看来,转学美国这个看似冒险的行为,其本质是求稳和求利。
余觅的目标明确——用更短的时间和更少的开销,拿到美国计算机本科学位,为在美申研与获得高薪工作提供助力。
“我高中就决定要去美国读研究生,本科提前出去利于我的申请,而且对比直接申请美国大一,本科转学花费的时间和经济成本更小,因为可以转学分。”她分析道。
在美国高校,学费和学时按照需要修习的学分设置。余觅毕业需要120学分,她从国内转了64学分,节省约46.9万人民币的学费开销与两年学时,基本可以按时毕业。
余觅不认为修习计算机是她的梦想,对比起来,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更像她心中的月亮。“要不是生活所迫,谁愿意敲代码?”她笑道,“头也秃了,人也丑了,也就是美国码农钱多还不用996。”
计划读美研是余觅留给自己的一次喘息机会,“其实当码农最好本科毕业直接找工作,读研浪费工作签。但我还没读够书,我还不想工作。”
关注退转学群体的初衷来源于孤独。
我在国内接受基础教育十二年,经历过高考,体验高等教育一年,在英国留学两年。我不再能与国内的同学感同身受,也不像一个早早接受国际教育的“正统”留学生——我英语基础薄弱,对欧美文化不太了解,却欣赏英国的高等教育培养方式;我热爱中国文学和文化,却不适合就读大学的课程设置。
作为一个矛盾的个体,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,我都是格格不入的。
余觅在国内高校面临相似情况,留美规划使她难以融入群体。
她所在的大学是山东的考研大校,校园中的光荣榜每年表彰成功考研上岸的学生。余觅刚入校时,榜单显示全院超过五百人的准研究生中,只有三人选择出国。一年后,她路过更新的光荣榜,发现一位留学生也没有了。
决定转学后,余觅成为同学中的异类,但她不以为意,“转学群体本来就是少数,不理解的是多数。如果一定要别人支持理解才能走下去的话,我觉得也不是很适合转学。”
“不安现状”或许是我与国内大学同学产生价值观碰撞的最大原因。刚入学时,起初也有几个同学表示不满意录取校,想要出国。但随着时间推移,那些学生时时抱怨,却好像也安于现状了。
我想少年人是一团热烘烘的火,放着光在天地间闯荡,“安稳”二字出现在人生起步阶段未免过早了。反思自己,我不想在十八九岁的年纪站在原地,一眼望到头。
陈最的处境更加被动,她在大二时感觉自己被孤立了。身边的同学早在大一开始规划考研、直博或者出国,但陈最无法务实考虑自己的发展。
她热爱未知的未来,希望能对将来抱有探索欲,而不是将人生稳妥地装在画好的格子里。“我始终处于一个探索阶段,很难针对规划给出一个准确答案。这导致大家隐约排斥我,因为我没有做出一个选择,不能被划分在任何小圈子里。”
大二时,陈最得知同学们按照规划组建了各自的群聊,互相交流信息和组织活动,而她没有被拉入任何一个群中,也没有人邀请她参与社交。
陈最感觉孤单,又担心自己被同化,她渴望尽情享受专业学习,过早考虑升学或就业对她而言是一种负担。
最终,陈最选择去英国重读大一,跳出固化的升学模式和国内同辈间无休止的竞争。“国外的同学年龄跨度很大,从老年到未成年都有,同年龄的统一目标消失了,我感觉自己放松了下来。”陈最说。
在三年的交往中,余觅对转学群有了感情,“我们已经从网友转变为朋友了。”她说。
2018年,她在QQ上搜索到创建于2014年的转学群,结识了如今在常春藤读博的群管理员何伟、在985高校学习计算机的章闰水、被调剂到土木工程转专业失败的祝政,以及其他背景各不相同,但志向相似的转学生。
余觅逐渐从需要帮助的新人成为转美群的领头人,她帮忙将群聊转移到微信,按照入学年份划分。如今,每个群都扩张到三百人以上,为更多难以寻找同伴的转美学生提供社交互助平台。
与陈最的相遇是奇妙的,我们互相填补了大学交际的空白。
坦白说,我和陈最有太多不一样——决定退学后我剪了短发,不再费心打理头发,早上抓两下,随手套件卫衣就出门;陈最烫着浅棕色的波浪卷,每日搭配不同的套装、鞋包和首饰,上学如走秀。我有点北京口音,话多嗓门大;陈最来自深圳,声音细柔但说话意外得耿直,常把我怼得生闷气。
即便如此,当我和陈最在一起讨论学业,聊起过去与未来;或专注当下,互相分享论文选题和思路时,我们都能感觉到旁人无法比拟的默契——应试教育使我们拥有相似的知识体系,而退学出国的经历又使我们更明确在本科阶段的需求,并珍惜得来不易的学习机会。
我和陈最有一门相同的选课,课上我们自动组成小组。“你们是我见过配合最好的一组学生。”每次报告结束后,导师都会惊讶称赞道。
多个傍晚我们一起走回公寓,街灯亮起,缓慢路过的红色双层巴士溅起积水。我有时会讲些喜欢的文学哏,陈最笑出声,我也跟着乐。
第一年课程结束后,陈最发信息,“感谢遇见你,李微明。”
我回,“我也很感谢遇见你,陈最。”
我享受在英国的学习生活——课表排满了文学阅读和写作课,偶尔有一两节自己选修的艺术鉴赏或者古典语言——都是我怀有热情去修习的。
我喜欢学校的图书馆,伦敦缠绵的雨声与古老的木质写字台,使我更容易沉浸于所阅所写的文本中。
伦敦的艺术资源使陈最沉醉,艺术史专业常设展览课,教师带领学生前去伦敦各大美术馆和博物馆现场授课,引导学生近距离鉴赏艺术品。
“比较遗憾的是因为疫情,目前无法完全享受伦敦的艺术资源。”陈最说。
当然,对我而言,留学生活并非完全正面。
作为文学专业学生,英文授课给我带来不小的挑战。尤其在国内上网课的一年中,我的听力和口语水平不可避免地直线下降。我有时不禁会想,如果我还在国内用母语上课,我也有极高的课堂参与度和流畅的表达。
网课结束后我去国内高校蹭了一节哲学课,我重新感觉到大脑像动力风扇一样快速旋转,而不是像扇蒲扇一样,时不时停下来想想这个英文词是什么意思。
我无数次问过自己后悔吗——
在突然忘记单词发音而尴尬停顿发言的时候;
在小组讨论中被本地同学排挤的时候;
在凌晨结束网课揉着眼睛倒在床上的时候;
但每想到第二天要讨论的诗歌、下周要上交的小说分析,我又觉得不后悔。
“再认真些,再努力些。”无数次反省后,我无数次提醒自己。
今年夏天,我写了一篇关于拉美社会分裂的文学论文,按照惯例去跟父亲讨论——在此之前他已经兴致盎然地听我分享过数十篇大大小小的论文了。在我简述完大纲后,他突然打断我,“我之前不支持你出国,”他说,“但我现在觉得,你留学的决定是值得的。”我笑起来,却又忍不住哭了。
当我采访到章闰水时,他说自己已经不想转学了。
他在去年四月份拿到美国Top30的offer,我看到了那条朋友圈,还点了个赞。“去年因为疫情申请不到美国签证,我想着在国内再体会一年。”他说。
就在这一年中,章闰水改变了想法,他放弃转学,打算留在本校。“自己迷茫的时候,专业知识储备不够,会认为是学校没有提供足够资源和引导。当我把自己丰富起来时,我发现可能上十遍这个大学,也不能把资源全用完。”
提起国内外的教育,章闰水认为更多是个人依照不同教育体系做出的偏好选择,“说到底是你想体验什么样的人生?在你的能力范围内,你想体验什么样的高等教育?我认为出国与否,本质是对个人选择的探讨。”最终,章闰水选择国内本科毕业后再赴美深造。
转学群中没有人非议他的决定,退转学的经历使走这条小众道路的学生理解,适合的才是最好的。
回国后,工作五年的秋林裸辞了高薪工作。“我暂时没有回到职场的打算,我需要想一想下一步怎么做。”她说,“我发现跟我同届或者上下届的美校同学基本都是这个状态。”
当年退学出国的决定帮助她度过高考挫折,但进入人生下一阶段后,秋林又面临了新的价值观冲击——与她随心探索的人生理念不同,秋林身边毕业于国内大学的同事基本从大一就开始思考职业规划,从学业到实习,每一步都坚定向目标前进。
“招新人的时候,我对照他们的简历,想着公司对于名校毕业或者业务能力的要求,总会想到自己当时没有去清华,没有复读,去了美国一所女校,学了个‘没用’的美术史。”秋林说。
她认为自己需要停下来再去自我发现。辞职后,她在国内四处旅游、拜访美校的朋友,通过友人间的交谈去重新思考过去、现在和未来的人生,“大家有时会去聊在学校里面学的那些‘没用’的专业,大家都说不上有什么好。但神奇的是,没有一个人后悔。”她笑道。
阔别多年,我和秋林重新取得联系。互相不知情的情况下,我们在本科阶段走出极为相似的道路。
“二十二岁,多好的年纪。”秋林在机场与我通话,她即将乘坐去往大西北的航班开启自驾游。“希望你到我这个年纪的时候没有我这样的困惑,”她笑着说,停顿了下又大笑起来,“不,你肯定会有的,我打赌你已经开始困惑了。”
我同意她的判断,但我其实欢迎困惑到来。
未来本就是充满未知和迷茫的,可能我们做出了当下适合自己的选择,觉得自己有勇气、想明白了,但随着人生进程的推进,会发现自己又活不明白了。
我想其实不要紧,不用害怕迷茫,对我而言,人生的乐趣在于探索,因为未知,所以热爱。
(应受访者要求,文中出现的姓名均为化名)
本文系原创文章发布,作者:李微明,文章所配相片皆为李微明所摄。欢迎分享到朋友圈,未经许可不得转载,INSIGHT视界诚意推荐
以上为华闻君推荐内容。